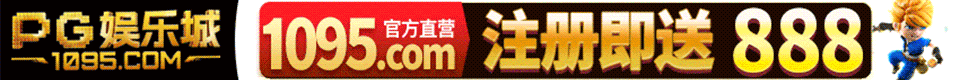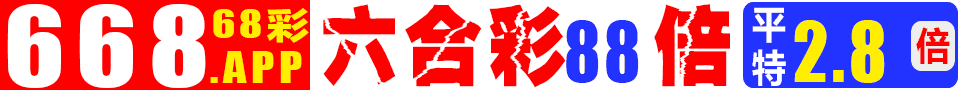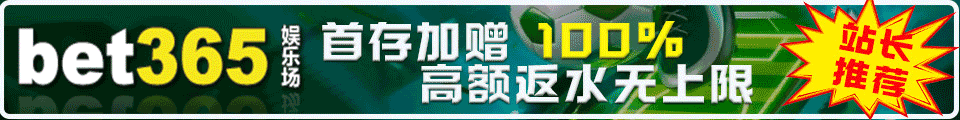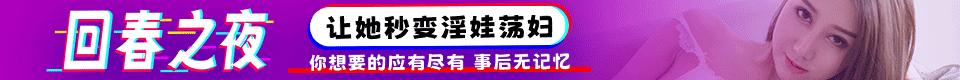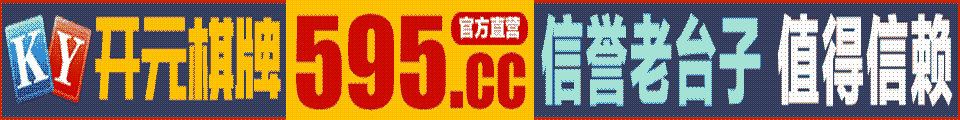七又二分之一
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汪妍的那天晚上,她被人灌了一肚子的春药,因此不仅 下身水流成河,连唿吸也狂野而杂乱。
若不是她被浑身上下绑了个结结实实,而 且嘴和耳朵也都被堵死了的话,她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现在她身边的男人。
比如我。
但我没有操她。
也许我本来应该那么做,但我没有。
取而代之,我用鞭子抽 了她一个小时,又拿蜡烛烫了她大半夜。
在她挣扎躲闪,知道徒劳无用之后的哀 号声中,我却恍惚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我想起了长风公园中绿草地上的秋千,想 起了黄浦江边渡轮的汽笛,想起了入冬以后冒着热气的糯米鸡,想起了初夏外滩 沿路如潮的人流。
与现实相比,往昔如此美好,记忆那么美丽,因此我想,我努力的挥动鞭子, 大概正是为了忘却。
那一晚我会出现在她的身边,完全是偶然,或者说完全是必然。
我和喜子照 往常一般轻车熟路的偷进一家客户的房子,随手取了些值钱的东西,然后把主要 目标——停在大门外的黑色奔驰开了出去。
我们当然还没蠢到在首都拿着偷来的整车去卖,连开到周边的天津或者河北 去卖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知道,还没等我们开到地儿,早就被抓不知多少次了。
所以对这玩艺,我们就随便找个小厂子一拆,光倒卖发动机零配件的钱就够我们 俩再晃荡上两个月的了。
我们俩一直干这些而没被发现过,靠的就是谨慎和不贪 财。
厂子是朋友开的,不愿意受牵连,所以拆卸的时候,也只有我和喜子在场。
步骤总是先上千斤顶,去了轮胎和轮轴,接着上焊枪,车壳整个的拆下来,变不 变形无所谓,反正是要当废铁卖的,再小心的拆发动机,把号磨掉,再逐个零件 的替换或者翻新。
每一次动手之前,自然要先清理车里的杂物,车屉里的私人物品,后备箱里 的东西,全都清出,能烧的就烧,绝对不随便扔,要不然民警同志一翻垃圾箱, 不什么证据都有了。
我们少说也搞过七八辆车了,什么档次的都有,但在车里一 般见不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家人的照片自然有,各种票据,罚款单也有,钱包一般都不会放在车里,但 我们也有一次看见一把锃亮的枪插在驾驶席的棉靠背里,当时我们几乎傻了眼, 敢情这车主还是个警察,丢了车是小事,要丢了枪那可真得惊动首都的公安局满 世界查了,我们俩说不好就惹祸上身。
好在厂子里也有各个号码的备用油,天也 还没亮,我们俩赶快给车加了油,趁黑又给人开了回去,以后几天都躲着不敢出 门,两个礼拜过去没什么风声,才敢又聚到一起,长吁短叹的说命大。
所以再做清理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小心。
我们几乎做好了所有的思想准备,想好了所有突发情况下相应的对策,但当 我们在这辆奔驰的后备箱里发现一个女人——而且是个被脱得一丝不挂,浑身绑 满绳子的女人——的时候,仍然面对面的呆看了半天,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我刚想开口问“怎么回事”的时候,喜子赶紧伸手捂住了我的嘴,示意不要 出声。
我随即明白,虽然后备箱里的女人戴着眼罩,看不见我们,可我一说话, 她就可能得知我们的身份。
安静了一小会之后,喜子轻轻拿起一把扳手,突然用力的砸在旁边一块铁板 上,响声把我都吓了一跳,躺在车中的女人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们由此确定, 她耳朵上塞的东西隔音效果不错。
从表情上看,喜子也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不自觉的压低声音嘀咕了一 句“这TMD怎么回事”。
车里放了其他杂物,大不了烧,可放了个大活人,这让人怎么办? 考虑半天,我说还是得连人带车送回去,喜子不同意,说躺在这的姑娘虽然 没听见咱们的声音,可肯定知道车被动过,回头她一说,车主就会找麻烦。
我还 是坚持送回去,一来跟公安局说车被动过,人家要问起何以见得的时候,车主想 必开不了口,二来就算车主想找咱们,也未必找得着。
喜子犹豫半天,才不情愿的回身去拿了一桶97号的油过来,我知道他挺失望, 毕竟少了一大笔钱。
刚才开了引擎盖子,看见里面的发动机上标着AMG 三个字母 以后,他还高兴的吹了一声口哨,要知道,那可是稀有货色。
眼看着时针指到两点半,再有两个小时天就该放亮,我们赶快驾着车往回龙 观的方向跑,离小区还有两三公里的时候,开始听见远处的警报声,附近着火了。
后来又跑了一阵子,警报声好像越来越近了。
喜子一个机灵,把车拐进了一条黑 黑的夹道里,告诉我原地等着,他一路小跑的去看看情况。
没5分钟,他又一路小跑的回来,上车就发动,往回去的方向开起来,边开 边骂着说,妈的那栋楼着火了,四周全是人,车一靠近保准被人看见。
最后车还是回到了厂子里,天也亮了。
我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办,他又回头揭开前盖看了一眼发动机,然后跟我说, 他要动手拆。
我说那这女人怎么办,他说你随便找个地方把她放下,警察发现她 也不要紧,到时候真正说不清的是她自己,没咱俩什么事,可这钱要是不赚就太 可惜了。
“我妈的药都断了一个礼拜了,浩子,我确实需要钱。
”他可怜巴巴的望着 我。
我看看他,再看看锃明瓦亮的奔驰,什么都没说,把女人抱起来塞到我的小 奥拓里,点火,临开车之前探出头来告诉他说,天亮了往大街上扔不好办,环卫 工人都出来了,我先送家里去,小区里住户起的晚。
明天夜里我再把她找地儿放 生。
“等我送完她回来帮你收拾。
”我告诉他。
喜子说好。
然而事实是我再也没见过喜子,等我八点多回来以后,他已经拿着拆下的东 西走了,我打他手机,关机;公寓电话,没人接。
赶巧这时候厂主过来,伸手就 问我要钱,他的厂子用一晚上两千块钱,他大概猜到了我们干的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他不管,也不想管。
我脸色铁青的好不容易凑出一千三给他,说余下的明天拿过来,现在没有, 他也就没好气的接了。
后来我每次想起这事,就会自己在心里说,什么他妈兄弟。
他拆那玩艺,也 就卖个八万块钱吧。
不就是八万块钱么。
我当时并不知道喜子就为那么一点钱便跑了,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我抱回家的 女人就是汪妍。
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们俩现在的人生大概会迥然不同。
可回头 想想,又觉得不对,即使我当时就知道,我也还会做那些事。
这不是命,这就是 我,是我这个人,我的性格,我过去的经历,决定了我一定会做哪些事。
彼时彼 地的机缘巧合只是给了我一个契机,使得我心中早该破茧而出的某些东西提前诞 生了而已。
当天我一肚子晦气的进了家门,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地板上蜷曲着呻吟的她。
我之所以觉得她是被灌了春药,完全是因为在我见过的女人中,也只有被灌了春 药的才会显得如此焦灼和燥热难耐。
她被塞了嘴,身子反弓着团团捆住,照理说 应该很难受才对,她身上嗡嗡作响的东西其实插在屁眼里,前面压根什么也没塞, 单单是这样,她还能不停的流水,就不得不让人佩服她现在的状态了。
尽管我很好奇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子,也很好奇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被人塞在 汽车后备箱里过夜,但是我可不想冒被人发现的险去揭开她的眼罩,或者除去口 塞问她几句话。
我应该悄悄的等,天一黑就赶快找个人少的地方,把她放下,等 着警察送她回家。
可我的眼睛还是忍不住在她身上游移,因为她的皮肤仔细一看其实相当不错, 四肢纤细,能够被弯成这个样子还不会感到太痛苦,说明柔韧性也极佳。
再看看 脸的轮廓,姣好,白皙,透着朝气,大概也注重保养。
就在我神游天外胡思乱想的当口,电话响了起来,虹姐噼头就问喜子哪去了, 打手机也没人接。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一早就没看见他。
虹姐那边沉默了一会, 说你现在过来,今天你跟郑媛的班。
我听完这句话几乎跳了起来,乖乖,平时都让我陪些名不见经传的姐妹出台,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也就是个蹲在门外等妓女收钱的命,想往上走难上加难。
郑媛 是谁,几乎算是北京“公关”圈子里最热的人物,只有喜子这种打架厉害,脑子 也清楚的人,虹姐才放心把郑媛交给他。
我三两下的把女人塞进衣柜里,怕万一有人破门而入,看出点什么,特意从 外面上了锁,转念一想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又把锁去了,然后赶快下楼钻进小 奥拓,去了虹姐的店里。
虹姐挺急,刚见面就直奔主题。
“晚上郑媛有个局,现在还找不到喜子的人,所以先拿你过来救急。
你现在 跟我和郑媛去库房里熟悉用具,两人练习暗号,多练习几遍。
要是到晚上六点还 不见喜子,你就跟着去。
” 虹姐这股雷厉风行的劲,像极了电影里的特工,她边说边带着我走进了库房, 郑媛已经等在里面。
“今天晚上要招待的是副部级的领导,地方是人家选的,所以咱们不能监控, 只能派人去出现场。
付钱的当然另有其人,内容也已经告诉咱们,郑媛都熟悉, 你可能还没见过,但时刻记住自己是艺束的人,别给咱们丢脸。
” 她等我微微点头表示听懂之后才又继续说道:“天下大,无奇不有,客人有 什么你没见过的玩法也要处变不惊,一切顺着郑媛走,她没有暗号你就不动。
但 是也要记住,一旦要动,就别留情,保护咱们自己人,保护郑媛,绝对优先。
” 我此时偷眼看了看郑媛,她正瞧着别处,并非不耐烦,只是冷漠,一贯如此。
虹姐继续说:“客人要用的东西大致是这么几种,开始之前每一样你都要试 过。
鞭子,要先拿你自己试,往手臂内侧抽几下,让皮肤红而不肿的才行;蜡烛, 必须是低温的,滴下来的不超过八十度,不然会伤人;电击的东西,36伏以下, 你必须试。
” 我又点点头。
“这一包用具都是咱们自己准备好的,客人的如果不合要求,就换咱们的, 保证安全,不给他们机会乱来。
”我更加努力的点头,因为这个时候郑媛恰好转 过头来,目不转睛的看着我。
“待会你就和郑媛练习,她的暗号我都熟悉,我在旁边看你听得对不对。
她 的嘴铁定会被堵上,所以只能靠发出的长短音间隔来判断……”虹姐继续说,我 也用心记,突然面对没见过的世面,还可能要处理自己没遇到过的情况,我有些 紧张,也有些兴奋。
“今天全靠你了。
”郑媛却突然说。
库房是个半地下室,墙角的窗子里难得透进一点光亮。
可那一刻,我也说不 清究竟是角度恰好的一缕阳光射了进来,还是郑媛转头时所带动的一点华彩,半 暗的房间竟然在瞬间变得异常明亮,我禁不住眯起眼睛,于是也变得不能确定, 她的嘴角是否真的露出了一丝微笑,那一丝微笑是否真的为我而来。